目录
快速导航-
文本探索专号 | 银鲑、灰熊、乌鸦
文本探索专号 | 银鲑、灰熊、乌鸦
-
文本探索专号 | 泥土的朋友
文本探索专号 | 泥土的朋友
-
文本探索专号 | 织霞山上
文本探索专号 | 织霞山上
-
文本探索专号 | 想起
文本探索专号 | 想起
-
结网纪事 | 唇枪舌剑与称兄道弟
结网纪事 | 唇枪舌剑与称兄道弟
-
结网纪事 | 黑山海岸日记(上)
结网纪事 | 黑山海岸日记(上)
-
结网纪事 | 求学心得
结网纪事 | 求学心得
-
心香之瓣 | 沪上书话二则
心香之瓣 | 沪上书话二则
-
人间走笔 | 读词记
人间走笔 | 读词记
-
人间走笔 | 客串
人间走笔 | 客串
-
新诗界 | 隐匿之海
新诗界 | 隐匿之海
-
新诗界 | 古人今诗
新诗界 | 古人今诗
-
新诗界 | 半明半暗的一天
新诗界 | 半明半暗的一天
-
新诗界 | 烟雨中的栾树
新诗界 | 烟雨中的栾树
-
作家讲坛 | 卖文为生,乐此不疲
作家讲坛 | 卖文为生,乐此不疲
-
理论与批评 | 马原的“元童话”,或先锋文学的未来
理论与批评 | 马原的“元童话”,或先锋文学的未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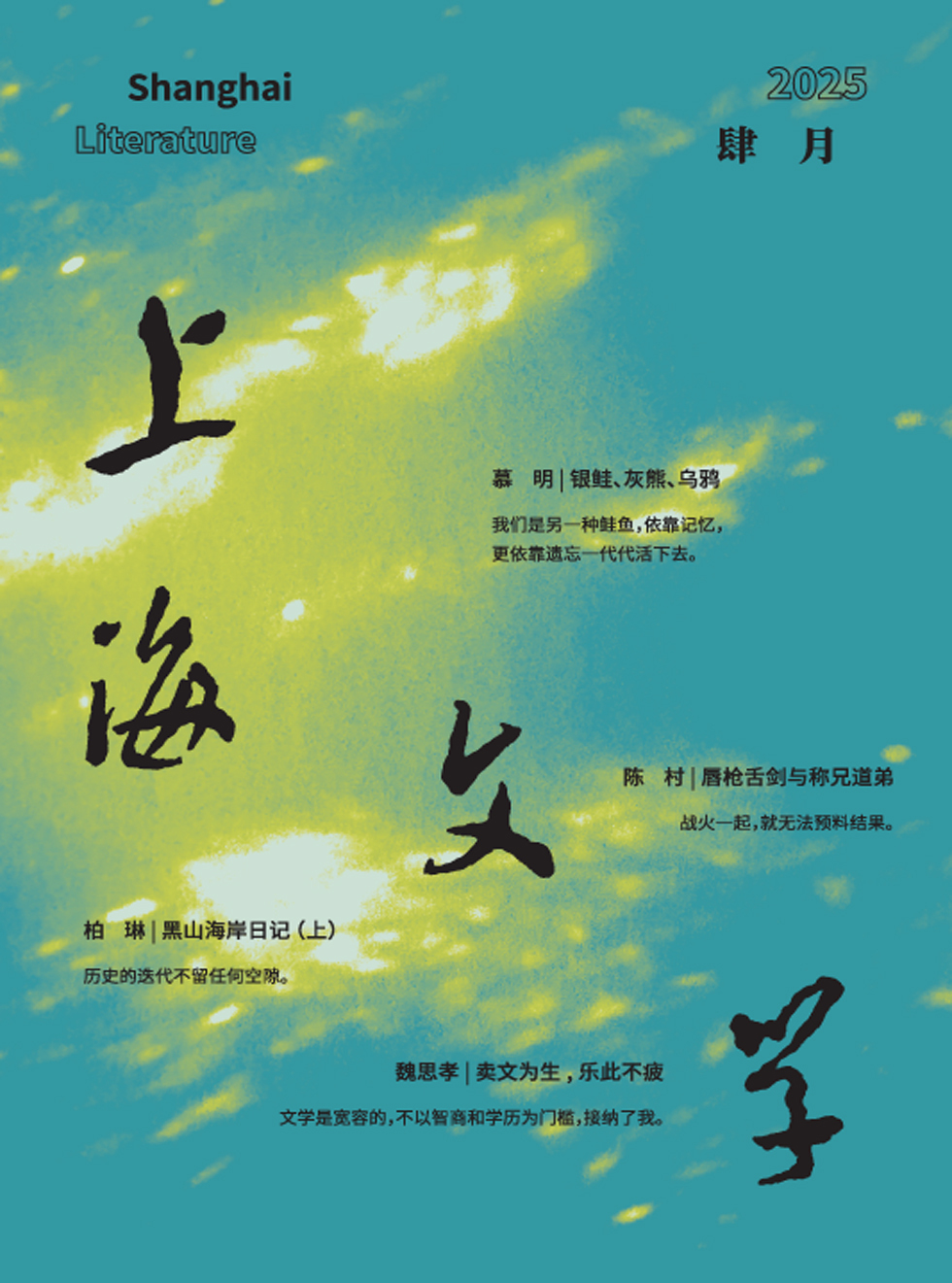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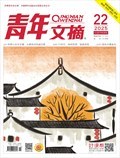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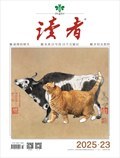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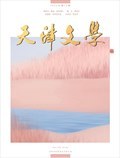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