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小说 | 千山之外
小说 | 千山之外
1 午后的书屋,刚下过一场急雨,暑气消散了一些,但还是闷热。入秋时分的杭州,正在经历“秋老虎”带给我们的炎热。室内所有空调都在吹着冷气,我在冷气的吹袭中插好一盆刚摘的鲜花,准备上二楼。 服务员快步跑下来,说,来了个很古怪的人,大热天的,非要坐在露台上,说是来找你的,你要不要去见一下他? 那个人就是阿卡。服务员对阿卡的到来深感好奇,又有点警惕。也难怪,长期在外风餐露宿浪迹天涯的阿卡,他的衣着
-
小说 | 一切顺其自然
小说 | 一切顺其自然
于晓威:鲍贝好。你的短篇新作《千山之外》就题材或形式来说,是一个跟“行走”有关的命题,或者说是表达一种“在路上”的哲学和人性。那么,你觉得在文学意义上,这跟当年的凯鲁亚克等人的“在路上”有什么联系吗?或者说,不同之处是哪里? 鲍贝:我的很多小说都跟我的行走有关,《千山之外》也是。也可以这么说,我的行走始终都在影响着我的写作和世界观。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,是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,也是人类
-
小说 | 泥塑之心
小说 | 泥塑之心
一 真是一个美妙的早晨。想想上午九点即将主持的重要会议,晨练的赵局长浑身充满了能量。脚上的运动鞋,多像一对飞舞的蜻蜓,在花丛间的石板路上掠过,轻灵到不留痕迹。早上六点至七点,是赵局长雷打不动的晨练时间,晨练的方式是快步走。赵局长的家在城区偏北部,小区背靠着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。小河蜿蜿蜒蜒,身材颇有几分婀娜。河水经过数度治理,清澈度能打个六七十分,不再像过去那般一副蓬头垢面的模样。夏天,会有难得的
-
小说 | 一路向西
小说 | 一路向西
那天,他车开到果子沟口时才发现,检查站已经封关了。伊犁他们是回不去了。 手机行程码显示他们新近经过疫区,所以,检查站拒绝他们过关已然言之凿凿。 无奈,他和他的温州大哥一起回到车上。过去未曾注意,果子沟口的旅店全开在检查站以内,出了检查站,除了那一家小卖店、一个加油站,还有一个汽修店和几排平房,几乎没有什么。 他们是去T市参加一个工程招标活动,但他们太天真了,以为公开招标就能中标。其实,公开招
-
小说 | 乌苏里江
小说 | 乌苏里江
一 傍晚他们到了虎头,直奔乌苏里江,他们就是为它来的。 然后,他们就站在乌苏里江岸边啦。 没来之前,她对它有过想象吗?想象过好多次了。现在,真实的乌苏里江就在她的眼前,她并不觉得和她的想象相近,奇怪的是,也未有落差。她一站在那儿,就把之前的一切猜想都放下,立马爱上它了——把它的前世今生都爱上了的那种。真的,就是这么不平常。 乌苏里江倒不算是一条大江,至少这一段不是。它缓慢流动,水波平稳。有
-
小说 | 小剧团
小说 | 小剧团
1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,冷到双腿刚迈出屋子就被冻得像两根木桩一般麻木起来,腿俨然只剩下了一个作用,那便是笔直地将身体和冰冷的地面连接起来,流动的血液瞬间宛如凝固了一般,门里门外仿佛是两个温度的世界。奇怪的是,这寒冷中不仅透着阵阵阴气,还似乎夹带着无数教人看不见的、细如发丝的针尖,无形地穿过肌肤的毛孔,直刺入骨髓,不消停地在其中搅动几下,远比那蚂蚁啃食更难受。 这样的寒冷倘若搁在平时就已很让人煎
-
小说 | 心里有鬼
小说 | 心里有鬼
一 喂,你是李兴明吗?季举朋猛地把电话按灭了,像要消灭一团烧身的火。 谁的电话?季举朋的爱人李芳在床上翻一本文学杂志,背着身问。 神经病。季举朋骂了一句。 又是找李兴明的?李芳转过身来看神经质的老季浑身哆嗦摸烟找火机。这一阵子骚扰电话弄得季举朋神魂颠倒,半夜三更睡不着。 兴许真是着急找人,你也不问一声,就挂了。李芳觉得季举朋这一点不像男人。 找个鬼。季举朋像被鬼缠着了。 这几天,这莫
-
散文 | 亲近的,遥远的
散文 | 亲近的,遥远的
夏秋二季,果实成熟的时候,果乡的学生便来邀请前往采摘,感受一下果实离树最后时刻的美感。果实和果实是不同的,它们来源于不同的树。明人江盈科认为:“桃梅李杏,望其花便知其树。”如果再加上口舌,更不会把果实混同。它们的形态让人惊异,有的硕大浑厚,有的轻巧秀气,有的剑?突兀,有的圆润委婉。至于色泽,虽然成熟时皆可以黄红二色喻之,但是在黄红二色范围内,却可以分出许许多多层次,让人下笔时踌躇着,着实词穷。每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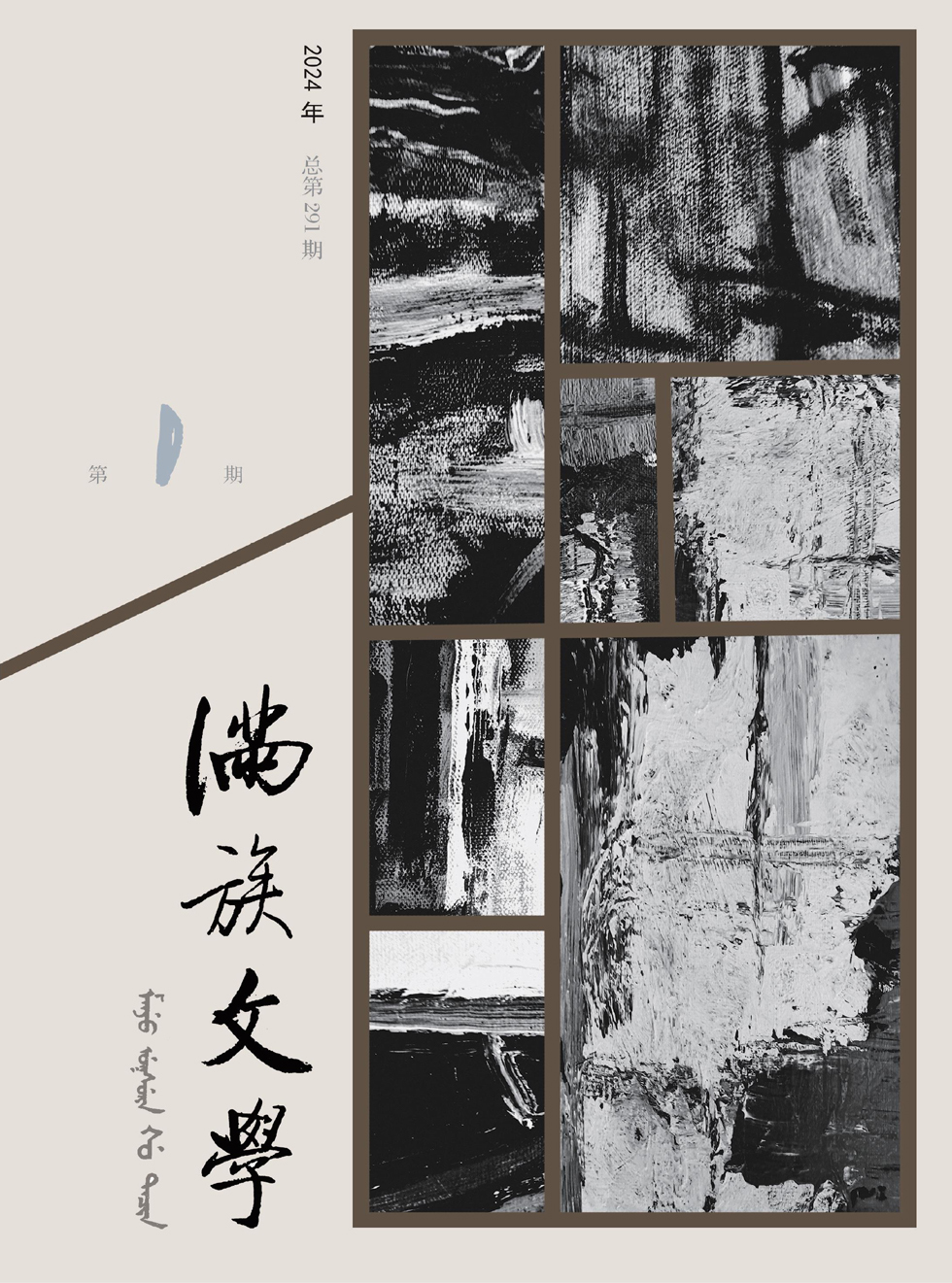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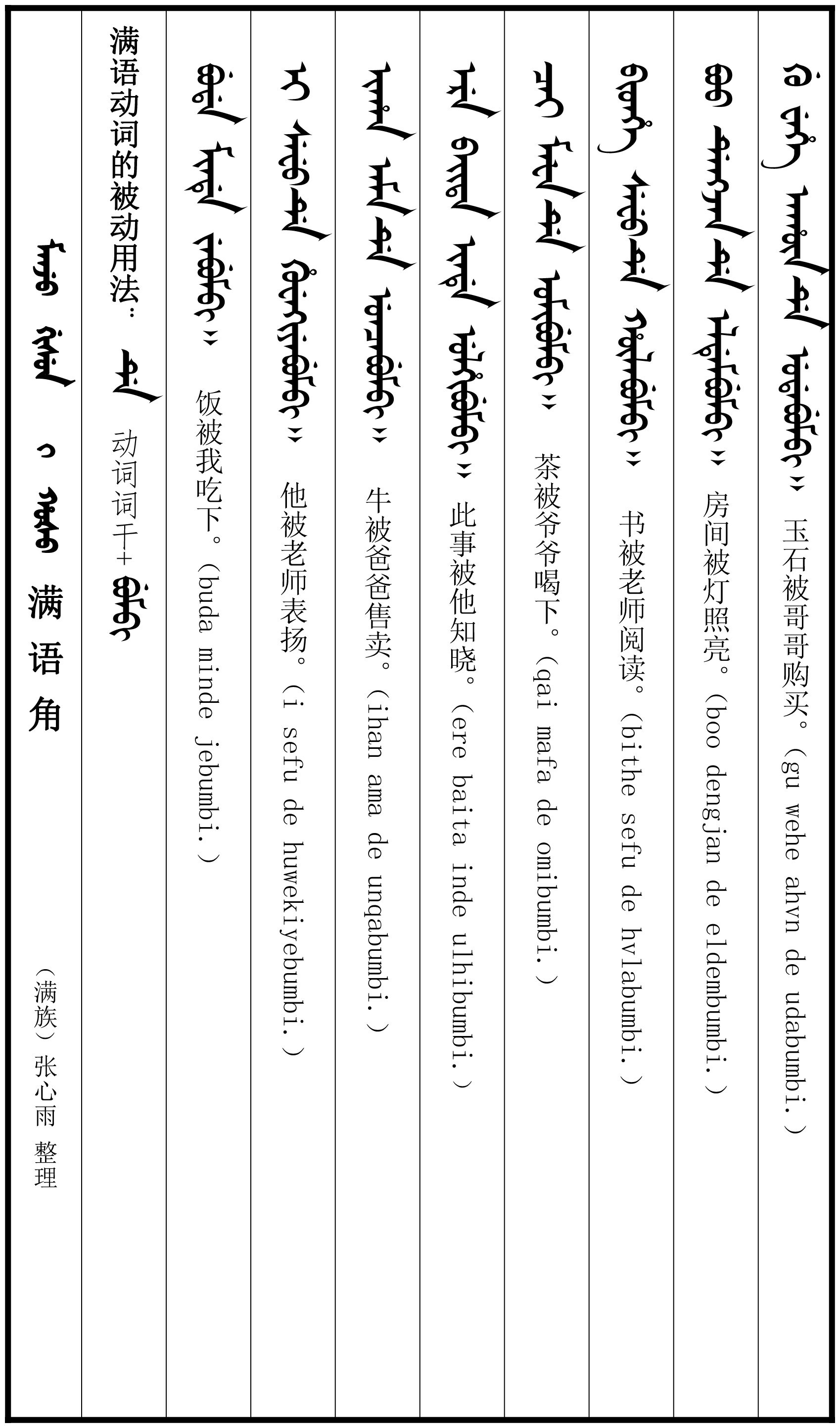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